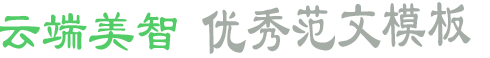梁实秋《寂寞》 寂寞是一种清雅。我在小小的书斋里,焚起一炉香,袅袅的一缕烟线笔直地上升,一直戳到顶棚,好像屋里的空气是绝对的静止,我的呼吸都没有搅动出一点波澜似的。我独自默然地望着那条烟线发怔。屋外庭院中的紫丁香还带着些许嫣红焦黄的叶子,枯叶乱枝的声响可以很清晰地听到,先是一小声清脆的折断声,然后是撞击着枝干的磕碰声,最后是落到空阶上的拍打声。
这时节,我感到了寂寞。在这寂寞中我意识到了我自己——时刻的孤立的存在。这种境界并不太易得,与环境有关,更与心境有关。寂寞不一定要在深山大泽里寻觅,只要内心清净,随便在市巷、小室都能感受到一种空灵悠远的境界,这被称为“心远地自偏”,意思是“心远则地也偏”。
在礼拜堂中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。伟大的庄严教堂里的钟声仿佛把我的心都洗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忧愁,我感觉自己的渺小——这渺小的感觉即是认识到我自己存在的明证。
朋友肖丽先生住在广济寺里,据他告诉我,在最近一个夜晚,月光皎洁,天空如清镜,他独自踱出僧房,立在大雄宝殿的石阶上,翘首四望,月色是那样晶明,苍劲的树木是那样的静止,寺院是那样寂静。他顿有所悟——悟到永恒,悟到自我渺小,悟到四大皆空的境界。
我相信一个人常有这样的经验:他的胸襟自然豁达寥廓。
然而寂寞的清雅并不是长久能享受的。它只是一次瞬时的存在。世界有太多的东西提醒我们:我们的两只脚踏在地面上,一只苍蝇撞在玻璃窗上挣扎不出去,一声“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这个瞎子吧”,都能使我们从寂寞中一头栽出;而“催租吏”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半夜来找人,都会使人感到沮丧。
至于自己内心内心的迷茫和焦虑,如果自己的心门不干净,随时都觉着是人世间的困境,就会更难享受这种寂寞。一个有高气飘零、隐遁的人,在从前的社会中还可以存在,甚至更被尊敬,但在现在的社会里,只有两种类型的人了:一是被泥泞的尘土裹挟的普通人;另一则是从泥泞中升起来喘口气的人。
寂寞便是供人喘出几口新空气。喘几口之后还得耐心地回缩进泥泞里去。我对此觉得并不 want 更为苛责,逃避现实,如果现实能逃避,我也愿意常努力以求之!
推荐阅读
查看更多相似文章